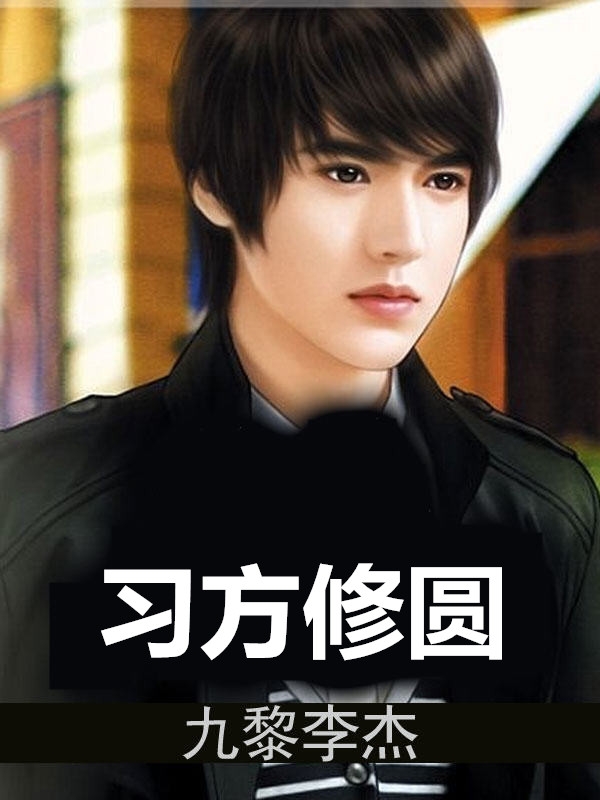有那麼一段時間,我老是看見一些奇奇怪怪的拇指一般的小矮人在田野裡駕著用八隻蝗蟲拉的小車偷運穀穗。於是我和家裡的大人們說了,大人卻將一頂“古怪的小孩”的帽子扣到了我的頭上。以至於在後麵我再聽見一盤水果聊天;再看見一個老頭拖著個黑箱子像收垃圾一樣從村裡的張老頭身體裡抽走一個透明的張老頭,然後張老頭就死掉;······我都裝聾作啞,報複似的不再和人講述。等到我漸漸成長,在為了諸如房子、車子、工資等等問題煩惱時,甚至連我自己也開始懷疑我在那麼一段時間是否真的聽見和看見的那些東西,還是我自己一味的臆想。我甚至還嗬斥過一個小孩,因為那時候我正在為擠公交車而犯愁,那小孩卻過來告訴我,它的甲蟲殼借七星瓢蟲去和蚜蟲打架了,它不知道回家該怎麼和它的媽媽說,希望我給它一句安慰的話作為鼓勵,讓它有回家的勇氣,我毫不留情的滿懷戒心捂著我錢包的對那小孩嗬斥道“我不管你怎麼回去和你那該死的甲蟲老媽解釋,我可沒空理你這小王八蛋,死遠點!”然後我擠上一輛沙丁魚罐頭一般的公交車,留下那個小孩獨自在車站抽泣。
但一個新朋友的出現讓我再次對我曾經的那些我自己都認為荒誕的事燃燒起深信不疑的信念。
認識這個朋友的時